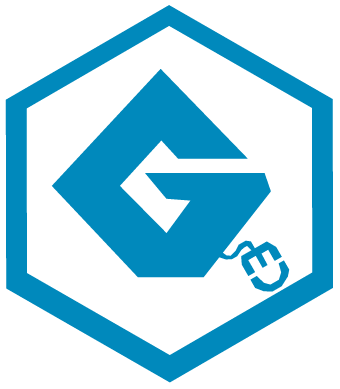注意自我保护,谨防受骗上当。
适度游戏益脑,沉迷游戏伤身。
合理安排时间,享受健康生活。
易中天教授的专题讲座《易中天品三国》正在央视第十套“百家讲坛”热播,受到了广泛的欢迎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但其中的一些分析也引起了观众的质疑。比如他对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空城计所作的批评,就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易先生认为,在历史上空城计是曹操和吕布作战的时候用的,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被诸葛亮抢走了“发明权”,还批评说:“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,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,戏剧作品也就一演再演,但是这个事情是不符合事实,也不符合逻辑的。……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,
第一,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,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,探个虚实可不可以?第二,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,琴声不乱,说明距离很近,看得见听得清,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?第三,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(引者按:易先生前面提到诸葛亮空城计最早是由一个叫郭冲的人提到的)和《三国演义》的说法,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,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,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,反正至少十万,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,围而不打行不行?何至于掉头就走呢?所以是不合逻辑的,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。”他前面说空城计的故事“实在太精彩了”,显然带有一种揶揄和调侃的意味,“不合逻辑”和“子虚乌有”的结论才是易先生的本意。但是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。我们知道,易先生讲的是历史,可他批评和颠覆的却是小说。
小说是文学作品,衡量历史和文学作品不应该使用同一的尺度和标准。历史是不能虚构的,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(哪怕是有历史原型的历史小说)则不仅允许虚构,而且应该有虚构。所谓允许虚构,并不是说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,而是指作家在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亦即进行典型化时,可以采用一些必要的艺术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如移花接木、改头换面乃至无中生有等等,都是不足为奇的常见手法。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,不仅是正常的,而且是合理的。当然,历史小说的虚构有一定的限度,与纯虚构的创作小说不同,“关公战秦琼”之类是绝不允许的。易先生说,空城计原本是曹操的发明(此点也有网友提出质疑,这里姑且不论),罗贯中挪来用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就有了问题,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即使事实确如易先生所说原本是曹操的发明,那也属于艺术创造中被允许的“移花接木”;就算纯然是“子虚乌有”,也并未违背小说可以虚构的艺术原则。
总之,据此并不足以贬损甚至否定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创造。更加值得注意和需要辩明的,是易先生关于空城计“不合逻辑”的分析。表面上看起来,他列举的三条理由确实很有道理。但这里牵涉到的仍然是历史和文学的不同标准。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,艺术有艺术的规律和特点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,就是它是审美的。中国的古典小说受传统的诗画艺术的影响,有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,就是它在塑造人物时,可以灵活地处理形神关系。一般来说,人物塑造要求的是以形写神,达到形神兼备。但传神(这里的“神”有较广泛的含义,既可以指人的内在的精神风貌、性格特征,也可以指作家在反映生活时所提炼出的生活的本质方面)是最主要的要求,有时候为了传“神”,可以忽略甚至背离“形”的某些方面,这就是所谓的“遗貌得神”的处理方式。苏东坡讲传神,就特别指出传神不必“举体皆似”,只要“得其意思所在”就可以了。(见《传神记》)“遗貌得神”的艺术处理,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中也是常常运用的,而且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例子,能给我们以思想艺术的启示。
我认为,《三国演义》所写的诸葛亮空城计,正是其中的一例。易先生所批评的三条,在《三国演义》所写的空城计里,属于日常的生活逻辑,在作者的眼里,算是次要的、非本质方面的“形”。他在创作时,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这方面的约束,也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,却在有意无意间,或甚至是自觉地予以忽略和背离,而去突出和着力表现他在对历史生活进行提炼时捕捉到的那个“神”――诸葛亮的大智大勇。空城计对诸葛亮的大智大勇,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的:第一,写他对兵法的灵活运用。兵法上讲的常例是,在战争中要“实则虚之,虚则实之”。意思就是在设在埋伏的时候要伪装成没有埋伏,让敌人钻进你预设的口袋;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却要伪装成设有埋伏,让敌人不敢进来。空城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,用的是“虚则虚之”,空城一座就明示敌人是空城一座,结果敌人反而不敢进来。第二,熟知并运用兵法上讲的道理: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。诸葛亮敢于采用“虚则虚之”的方法,并能够断定敌人在他的引诱和迷惑面前不敢进来,是因为他对对手司马懿深有了解。司马懿是一个聪明的、懂得兵法、并且富于军事斗争经验的人物,他以兵法常规的“实则虚之”来判断,当然不敢贸然进城。
诸葛亮还知道司马懿是一个对自己十分了解的人物,诸葛亮一生行事谨慎,司马懿当然也不敢相信他这次真的是在弄险。如果对手换成一个头脑简单而又不懂兵法的人物,那空城计自然就唱不成了。第三,诸葛亮临危不惧,镇定从容,在空城一座而又面临大兵压境的情势下,竟然能如易先生所说“神色自若,琴声不乱“,因此,虽然实际的处境十分危险和被动,却反而让人觉得他在精神和气势上超过甚至是压倒了对方。读者读《三国演义》,从空城计的艺术描写中,具体生动地感受到了诸葛亮的大智大勇,由此获得了审美的愉悦。他们看到司马懿退兵了,诸葛亮的冒险真的奏了奇效,心里会感到非常的快乐。试想,要是司马懿真的采用了易先生三条中的任一条,破了城,或一箭就把诸葛亮射了下来,读者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?实际上,读者在欣赏这段艺术描写时,是不大会(也没有必要)去考虑和计较还有什么地方不合逻辑的,而是宁可相信,在那个特定的艺术情境之下,司马懿是被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机和精神气势给“震慑”住了,他不敢贸然入城,一阵犹豫之后掉头就走是完全可能的。其实,这种“遗貌得神”(只里的“貌”指的是次要的、非本质的生活形态)的描写,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还不只此一处。
第四回里写曹操杀吕伯奢(京剧改编名为《捉放曹》,舞台演出也是长盛不衰)也是一例。曹操谋杀董卓不成,在逃亡中到其父执吕伯奢家,受到吕伯奢的热情款待。在吕伯奢到西村买酒时,曹操因误会而杀了吕家八口,而在明知错杀的情况下,又在出逃的途中杀了买酒回家相遇的吕伯奢本人。最后在陈宫“知而故杀,大不义也”的斥责之下,引出曹操那句著名的人生信条: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。”这段情节突出地描写了曹操的不义和残忍,开篇不久就为曹操形象的塑造定下了一个基调,短短的一段描写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但其中也存在“不合逻辑”之处:吕伯奢家中那么多人,在来了这么一个贵宾(结义兄弟之子,杀董的义行又那样令他尊敬)的情况下,没有必要将客人撇在家中不陪而亲自去买酒。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出于极写曹操不义性格的需要而设置的。但是除了少数专家在考察《三国演义》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时论及外,一般读者是很少注意和计较的。
《红楼梦》中则有更为出色的范例。已故著名红学家吴组缃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小说有神似的传统时,曾对黛玉葬花一段描写作过精彩的分析,他说:“黛玉葬花,一边哭着,一边念着葬花词。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,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,把它一句句,一字字记录下来,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,这就不形似。……黛玉葬花,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。为什么葬花呀?她在怜花。为什么可怜花?她在可怜她自己,就像一朵花一样,在那样恶浊的环境里,她这么一个女子,这么一朵美丽的花,就要被摧残践踏为污泥了。她想把花埋起来,‘质本洁来还洁去’。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,一个‘意’,一个神。在这种情况下,丢开了形似,而只抓神似。黛玉葬花,构成了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,就因为它画了神。”(见《说稗集》)《红楼梦》不只是细节,就是一些大的构想和设置,也有它有意无意忽略的一面,要是从日常生活的逻辑来看,也可以当作所谓的“疏漏”来批评。就说大观园吧,又有北方园林的特点,又有南方园林的特点,弄得想寻找大观园原型地址的人扑朔迷离,无从查考。又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,表现了那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,体现了建立在共同思想和人生追求基础上的近代爱情观念的特色,可是若要细究呢,贾、林二人的年龄曹雪芹就写得模糊不清,大约也就不过是十二三、十三四岁的小孩子,这哪里能呢?
再说这不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早恋么,为什么还要去肯定它呢?还有他们近亲的姑表兄妹关系,从现代优生优育的观念来看,也是不能恋爱和结婚的,要从这么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,贾母、王夫人等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们的结合,也算不得有什么大错。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提出问题,去指摘甚至否定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描写,那真是只见皮毛而不见神髓了。所幸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位读者这样去较真,硬要要求文学名著里的艺术描写同生活必须“举体皆似”,处处都要严格符合生活的逻辑。易先生说空城计的故事在文学作品里是一说再说,戏剧作品里是一演再演,这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,而且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事实。这说明,人们对《三国演义》和舞台上演出的《空城计》是认可并欣赏的。其原因,就是他们用的是文学的审美的眼光,而不是历史的眼光或一般生活逻辑的眼光,只要能从中得其“神”,获得思想的启示和审美的愉悦,就可以见大而略小,得神而遗貌了。其实,自从《三国演义》问世以来,就不断有人用历史的眼光和标准去批评它、颠覆它。其最著者,如明代的胡应麟就称《三国演义》“古今传闻讹谬,率不足欺有识。”
乐趣网 卧龙吟 官方网站: http://www.lequ.com/wly/
乐趣网 H5游戏平台: http://www.lequ.com/
玩游戏,找乐子,就上乐趣网!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,请点击收藏乐趣网卧龙吟
上一篇: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
下一篇:欢乐三国志——关羽最后的安可曲

 经典三国游戏背景,玩法多样的战争策略,属性随机的神兵利器,彼此克制的各系兵种,此款绿色页游能让你体验最纯粹的战争游戏。
经典三国游戏背景,玩法多样的战争策略,属性随机的神兵利器,彼此克制的各系兵种,此款绿色页游能让你体验最纯粹的战争游戏。